[ˇՓ���о�] 70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Ј���׃�Ї����һ��(�M�D)
��4 ���� 3381 ����x 2015-11-26 07:39 ��(bi��o)��: article һ���� style �Ї� ˇ�g(sh��)��
�� 1990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1970 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_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ǡ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ľ�ʮ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ǵ��ˡ��ഺ���ᡱ�L���Į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_���Wꖴ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Ї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һ���µĕr(sh��)�ڣ�
���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 ����ָ 1970 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o���гɞ��Ј���׃�Ї�֮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ͬ�ı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׃��ζ���Ј���׃�Ї�֮���һϵ�и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x��׃��
�����ʘ��Ļ���׃�Ї���ؔ(c��i)���ֻ���׃�Ї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׃�Ї���ȫ��׃�Ї����W(w��ng)�j(lu��)��׃�Ї��ȵȣ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Һ;���ģʽ�ĸ�����׃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׃Ҳ���팦�@һ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ĸ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ɴ����ھ�ʮ���ĩ��ʽ���_�ˡ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Ļ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ì�ܺ͒�����̎�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ڵ����Ҿ���
����1990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ĸ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ͺ����R�ΑB(t��i)�w�Ƙ�(g��u)��һ�N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ij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(qi��ng)ʢ�ͳ�M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ΑB(t��i)�Ľ^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w��ȫ���Ļ��Ϳ����˾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Ʒ�ڴ��ͳ����Ј���؛���ϱȱȽ��ǣ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��Ļ�
�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Ĵ�Ҏ(gu��)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̘I(y��)�Ļ����о��ҕ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W(w��ng)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ϱ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к�߅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֮�g�ĵط��ԣ��ȵ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һ��̎�ڇ��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ŵĕr(sh��)�ڣ����@һ�M(j��n)��ͬ�r(sh��)Ҳ���S��ʹ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ﻯ�� 1990
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s��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M(j��n)���Ĵ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?y��n)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ٱ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A�ӷֻ���ʹ�@һ
�����ഺ���_ʼ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һ����δ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ì�ܺ͒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ɱ���ط�ӳ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ڵ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x��ʽ���J�룬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ڏV�|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Ĕz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ڱ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Ї�С�ǵ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Ԣ�ԣ��@��ԭ��̎��ǰ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С������һҹ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ڡ��о��ҕ��
�I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R�]�Ӱ����۸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һȺȺ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ͺ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İ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�һ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µ�
���w�Ԙ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|���ϿյĹ��¡�����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͉��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ǘ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Ь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_ʼ��ӳ�@һ�r(sh��)���Ї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о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ij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Ʒ�м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ͬ��Ҳ�[��һ�N���ҸЂ�ɫ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܁�
���@�N�µ��M(j��n)��׃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�S�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70 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ഺ����Ĵݚ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��ґB(t��i)���Ժ����Ҳ���ܵس��F(xi��n)�ڴ���P(gu��n)�ڱ���ҹ����Ůϴ���g�ļo(j��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Ľ�ȡ����ӱ��ķ�ʽ�����ʬF(xi��n)
������o(j��)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Ŀ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Q̽��һȺ�c��ͬ�g��Ů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һ��ҹ����ϴ���g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Ů��ƴ���ػ��y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
Ԓ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?c��i)?sh��)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ֱ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Խ����ھ�ʮ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�L�е���Ҫ��ɫ�͏V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ֱ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ϴ���g��(n��i)�ġ���(zh��n)
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]��ֱ�ӵ�����u�r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��h��Ů�����x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 70 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_ʼ��(zh��n)�_�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ꖺ��x���Ǟ�����ġ��ഺ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˵ĵLj������ഺ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Ҳ�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�Ŀ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Ě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_ʼ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҃�(n��i)�ı���ijʬF(xi��n)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Ҳ�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^�����D��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L(f��ng)���ҕ�XȤζ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һ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ꖹ��µĸЂ��к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|�еķ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� 1998 ��ǰ�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ꖺ��x���ǵĹP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ɞ顰 70
��һ����(bi��o)־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ꖱ��F(xi��n)�ˡ� 70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ꖹ��n�����Ԏ��Ђ�������ì�ܶ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ڱ�����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DŽt���F(xi��n)
�ˡ� 70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(n��i)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к�ʹ�ࡢ���]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d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挦һ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Ѫ�Ⱥ����Ժڰ��ķ��]���g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ഺ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ꖺ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ȫ���ڡ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ģ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ģ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�ġ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ͬ�����ڔzӰ���L���͵��ܵȷ�����u�γɡ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ϵ����ꖹ��µĸЂ��к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|�еķ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ģʽ��ӳ�ڮ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ʧ��ʹ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Ԍ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ʽ�ʬF(xi��n)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P(gu��n)�ڃ�(n��i)�ĵ�Ԣ�Ա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sh��)��Ҳ�_���ˡ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Ԣ�Ա��F(xi��n)��ʽ��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@�ɂ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ڡ� 70
��Ⱥ�w��ʽ�γ����Єe����һ���ĵ��º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]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ģ�Ҳ�]��ʲô����ȫ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y(t��ng)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@
�N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1990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M(j��n)���ļ��wҪ���ֱ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ȱ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µĸ�Դ�͔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ഺʹ�ಢ���� 1980
����ǘӿ�����һ��ֱ�ӵ��ƶȿ��Թ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B(t��i)�ȵ���һ���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���Ҳ�ڗ�|�ı��ݔzӰ�����һ��֪�R���ӡ��еõ������_�ı�ʾ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ΑB(t��i)�ĵ��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 70 ��һ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ھ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ı��|(zh��)�ό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�һ�NԢ���Ե����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ϵ����ұ��y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ԣ����ഺ���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 ��һ�����L�� 1990 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ʮ�ꌍ(sh��)�H��Ҳ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γ��^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̓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˽�˿��g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Ԣ�Կ��g��̓�M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 1990
����к��ڳʬF(xi��n)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˸��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˱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ʹ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ԏ�����Ͷ��б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˽�˿��g���ҵ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ڵĴ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ijЩ���g�Ě����ԺЂ�ɫ����̎���Ї�
�Ϸ��ďV�|���Ї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γɵĵ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1990 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_ʼӿ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Ӱ푵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־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ڸ��صġ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Ǵ�Ҏ(gu��)ģ�D(zhu��n)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Ժ�Ԣ���Ե�ҕ�X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ă�(n��i)�Ě�������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誵ȡ�
�����ΰ��ġ��P(gu��n)�ڕr(sh��)�е�ʮ�傀���ɡ�ϵ�в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g(sh��)�ڡ����п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̓�Mһ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ɞ顰 70
���ഺ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^��zӰ����Ę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Ů������ 1990 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S�ࡰ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ζ���_ʼ���c���H���г����ġ��ᡱҕ�X�����ᡱ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Ҳ��ʽ�ɞ顰 70 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 1990
���ĩ�_ʼ���F(xi��n)�Ϸ����Ì��Լ��b��ɕr(sh��)��Ů�Ե���ȻδÓ�M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һ���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˳��е�ȥ�ط�
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Ů�Եļ������Һ͵ط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ĸЂ���w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п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ڗ��º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Ʒ�б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x����һ�N̓�o�Ե��ഺ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µġ��ഺ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ϵ���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u)Խ�����ڰ��I(l��ng)�Ϳ�
Ů���Ķ���̓�o�С����R�^�µġ����п�Ů����Ҳ�_ʼ�ʬ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��H���К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Լ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ն����Իà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ֵı��ݔzӰ���o�}��Ҳ
���F(xi��n)�˴����鼆�Ķ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Ĵ��Ĺ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µ�̓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Video ���U�桷�t���_(d��)�ˌ���ɽ��С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в��w�ĸЂ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쳵� Video
���Y־�ĔzӰ�tԇ�D��Խ���ڶ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ഺ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һ���Գ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Ļ��Q�еı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쳵�
Video
�����һ�NԢ�Ա����鹝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O�ȉ��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ճ��ԡ��Y־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ˡ�ϵ�в�����һ�N�dz����Եı�
�ݔzӰ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��ҷ��]���ճ����ָк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zӰ�Ĉ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۸ij�̓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ഺ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ҵij��L�龰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ʬF(xi��n)�ˡ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ǰ�l(w��i)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 70
��Ⱥ�w���L���ĈD���^��͔����Է���ČW(xu��)Ժ�Ɍ�(sh��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һֱ�ԈD��Ĕ���(sh��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d�w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|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µ����ҳ��L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̎��
�����͡�С�R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ڤ�룬�Լ�һ�N���Q���Ԋ��Ե��殐�����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U(xi��n)���͡����ӵĽ�ጡ��Ƚ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Եđ�˲�g���@
�Nҕ�X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ԇ�D����һ�N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̓��(g��u)��ͬ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ָ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߀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߀ԇ�Dʹ�D���鹝(ji��)̎��һ�Nֻ�ЬF(xi��n)�ڕr(sh��)�̵ļ���͏�
�����s�]��ǰ�����ġ��жΡ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IJ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ġ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ؽС���ԇ�D��һ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ӵ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(j��ng)�|(zh��)
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漰ͬ�ԑ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ƻÃ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ҳ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(c��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˻��IJ��B(t��i)��(sh��)�(y��n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˵��L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Ϸ�ӳ���ഺ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֮�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ֱ�ӳʬF(xi��n)���ഺ���ᡱ��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ұ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̓��(g��u)�ԅ��c���Գ�һ�w��ҕ�X
�횤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 70 ��Ⱥ�w�ڹ�ͬ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w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R�ΑB(t��i)�ϲ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ǘӵĚvʷ���ζ��ϵą���ϵ���@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҅��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ʽ���ɞ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ҕ�X��ʽ��
�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֮�g��һ�N̓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ʽ���H�H�Ǟ��˱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ҽ^����ʹ�࣬��ij�N�̶���߀��һ�N���y��ʽ���»÷�
ʽ����һ�Nҕ�X�r(ji��)ֵ�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ҕ�X��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ø���ص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ഺ���ᡱ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w��Ԣ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߀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 /
�Oԭ�ĽY(ji��)���b�úͶ�ý�w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ݿ�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һ���O�䚈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硶���`�꡷����Ȯ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(zh��n)ģʽ��ʹ���˸��N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t�O(sh��)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/ �Oԭ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ഺ�w�(y��n)�ИO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ڡ� 70
��Ⱥ�w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ȫ�]���ζ��Ϻ͚vʷ��ҕ�X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º�ꐲ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L�����}��(j��ng)�䡷ϵ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һ�N�c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ڽ̵������Ԍ�Ԓ��̽ӑ
��ߺ�֪�R�����Ե�˥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µ����Һڰ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ꐲ����L���t�ǽ���һ�N�vʷ���(y��n)�ķ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ļ��w���^�;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˱���ĺ��塢��ʮ��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Լ���һ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ؘ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Ļ�ɫ�����͞��а�ľ����u�r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硶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70
���ښvʷ���ζ��ϵ��P(gu��n)ע��Ȼ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ġ��жΡ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Ј���׃�Ї�֮����Ҳ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c֪�R���ӵĚvʷ�Ժ��ζ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˴�Ҏ(gu��)ģ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
һ�N�c���Қvʷ�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ܵČ�Ԓ���S���@�N���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o�ɱ����Ҫ�M(j��n)��һ�N�vʷ���ζ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ȱʧ��̽�L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䱳����Ȼ��ӳһ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γɎ��o�� 70 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ʹ��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һ�_ʼ�H�H�����ڬ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һ�㻯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_ʼ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Ժͱ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D(zhu��n)׃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ˌ��ڬ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D���ֱ��ʹ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ھ��w���L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ı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͵���
�龰�ĸ������@�ǡ� 70 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ĵ�һ���A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1990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Ě����Ժ��ഺ�Ԍ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�u�ġ� 70
��һ���ܶ��˵���Ʒ�е������_ʼ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@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ꖡ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˵Ľ�����
Ʒ���@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 1970
�����ǰ�ڳ�����Ⱥ�w�ھ�ʮ���ǰ�ڵ��ഺ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͘O�ˬ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ڽ�(j��ng)�^�ഺ�����ı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Ԣ�Ե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_ʼ�����c�vʷ��
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Č�Ԓ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 �f �ġ����ɶȡ�ϵ�ДzӰ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�
70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A����ҕ�X�ϲ��نμ����F(xi��n)ʹ��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F(xi��n)һ�N�ڮ�(d��ng)���Ї����˴��ڵij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ʹ���Լ�ҕ�X�ϰa
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Ⱥ�w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ҵ�ҕ�X�ϵij��(y��n)�Ժ��»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_���Wꖴ�����ëë��ٺ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 �߬r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ഺ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ǰ�l(w��i)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Ҳ�ǡ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һ���µķ�����ͻ�ơ����ij��F(xi��n)�c�ձ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ڇ��H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]��ֱ���ܵ��ձ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Ӱ푣�
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ʮ���γɵĴ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A(ch��)֮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g�ӻ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 1970
����к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L��һ�����R�]�Ӯ�Ƭ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뽛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�L�M(j��n)�̣�ԇ�D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ؔ(c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渂
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»������¾��ķ�ʽ���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硣�@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Ҳʹ�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ό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Ҍ����ߵ��˘O������ҕ�X�^����L���Եȷ��潨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w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����δ��һ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c(di��n)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ҵ��˲��؏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ͮ����L��ԭ��(chu��ng)�Ի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ϣ��t����һ�N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ڵ����Қ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R�Α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ҕ�X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o����(x��)ā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ݚ�Ϣ��ͬ�r(sh��)Ҳ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ʹ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_�ġ��ڸ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@��һ�N 1970
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˵�̓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x��)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Ϳ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õ�̓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_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L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_���ˡ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һ�N���¡���ʹ�ཛ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ڸ߿����I���Լ��Ԛ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ഺ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Ў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ҕ�X��
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Wꖴ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1990
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_ʼ�Lԇ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µ��L���Ԍ�(sh��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ڵġ���܊��ϵ���nj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r(sh��)�ڵġ���܊������͑�(zh��n)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����䡶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ԇ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x���ͮ��P�|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ϡ��Wꖴ��ġ���܊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˚vʷ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Ŀ�е��Α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ă�(n��i)���f��(y��n)�Ե���ʧ��
�����c�Wꖴ����ڡ���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¸������Ƶķ�ʽ��
�߬rҲ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ġ���؈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µ�ҕ�X��ጡ���؈�o�ɳɞ�߬r�@һ����׃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挦�o�g�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С�Y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ٺ��
Ȫ�ġ��ҵ�ɽˮ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ɽˮ����һ�N��˹�ṫ�@ʽ�Ŀ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ڡ�
70��ɽ�����t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е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ٺ��Ȫ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е�ҕ�X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ϵ�С�����߶�����С�ˡ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Α�Ŀ��g���ֺͿ��Ա��ٿv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һ���Ŀ��g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䌦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̓�M��
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ɸ��N�xҎ(gu��)���ĵ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И�(g��u)�ɵ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���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½M�ϵ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̓�õ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eֹԎ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
���L��һ����Ӣ�Ļ�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Ҳ�Ǫ�(d��)����Ů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κ���һ���˵ij��L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ģʽ����һ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ǘӱ���С���d�ɞ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˲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d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ʹ�Լ��옷������،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^�ڼ�ͥ�͌W(xu��)У���ܹĄ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Շ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ж�ô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һ̤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L�γɵľ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о���һ�NԢ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Ƥ�µĿ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е�̓�o�У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M(f��i)�г��L���@һ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̎��(y��u)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o߅�H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Ѫ�Լ�̓�o�Ў����ںܶ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̓�M�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Ǻܬ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Ƿ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]�����w֮ʹ�ĺܿ�ͺܿ�е�ʹ���@�Nʹ��
���ڡ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г�Ҋ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һ���б��F(xi��n)�ø��ص���Ҳ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еĽ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䐂�Ў�һ��ӿ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
��(sh��)��̓�o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ںϣ����換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ҕ�X�ϰa�ԡ��@Ҳ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еġ����@�Α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N̓�M�ı�Ű����
��ı����У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@һ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ډ��ֵij��(y��n)�Ա��_(d��)��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ĈD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һ�N���һ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Ӣ��ҕ�X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Ԍ����@�N�D���ҕ�X��О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ҕ�X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c�����Į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Ļ�
Ҳ����ֱ�ӵ�ͬ���ԣ��M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Л]��һ�N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ij��L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m���Ї�һǧ���ԁ��δ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wϵ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ȫ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x�_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Ї��H�Խ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
����߀δ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ΑB(t��i)��ȫ�_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ԡ��@�N�p����ʹ�@һ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һ�N�µ����ҿ��w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Ј���׃�Ї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Й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@һ���ٵ�׃�����Լ��@�N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pһ�������қ_�����@�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ϴ_��(sh��)�ǚvʷ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Q���o�@һ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�Ҳ��ӳ�ˡ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Ȼ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˼��ͷ�ʡ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ϣ��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ϵĴ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ԣ��Լ����o�vʷ���ζ��ό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Ҫ��ӳһ�N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 1990
���ǰ���ǘӻص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ԵČ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ǂ��A��Ҳ�ѽ�(j��ng)�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ĽK�Y(ji��)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³����� 1990
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F(xi��n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棬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cʮ��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ǰ���Ї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y(t��ng)�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ϱ��C���o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ΑB(t��i)��ģʽ
Ҳ���ٿ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վ��һ���µ�λ���ό��Ү�(d��ng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^��Č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��ô_���ܵ��_ʼ��һ�N�µķ�ʽ�̓A���@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ڡ�
70
��һ���_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c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ʷ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Ҳ��̫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֪�R����ʽ�ij�߽Ƕȡ�����һ�_ʼ�ͺ܌�ע�����ҵı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ij��L�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Ќ����m���@
�N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y�r(ji��)ֵ��ҕ�X��ʽ���@һ��ʽʹ�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Z�Ԏ���Ҏ(gu��)ģ�ز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Ժͱ����Եķ�ʽ�����ֶ��ϣ�ʹ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ý�w���zӰ��
Flash �Ӯ��Լ�Ӌ(j��)��C(j��)ý�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Ҳ���ُļ�ˇ�g(sh��)�ĽǶ��M(j��n)�Ѓ�(n��i)���Ե����h��(sh��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Ǐ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һ�N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h��(sh��)�(y��n)���L���ĈD��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ý�w�Ӯ��Լ�Ů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˴����Č�(sh��)�`��
�����ڡ� 70
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ǵ��˵ġ��ഺ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ڈD��zӰ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_���W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ëë���ˌ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ҕ�X�Ĉ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ڈD�����ԵČ�(sh��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߽��ڵ��L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(y��n)��Ҫ����ģ�Mһ�N���(y��n)�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Ո��С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
���ڄe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1990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Ҫ�D��(sh��)�(y��n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ڈD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Q�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D��P�|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ԭ��(chu��ng)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ë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Ę�(g��u)�D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ĈD��ԭ��(chu��ng)�ԡ������ԵČ�(sh��)�`߀���� Flash �Ӯ��͵��ܷ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� Flash
�Ӯ������ڌ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Y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ġ���(qi��ng)�I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·�ϵēu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ΰ����˵Ŀ�ͨ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 1990 ���ĩһֱԇ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l(w��i)ˇ�g(sh��)��(sh��)�`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hˇ�g(sh��)Ⱥ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Ɲ������n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һ����Ů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ý�w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ͬ�ԑ��}�ĵȷ��涼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Č�Ů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ˇ�g(sh��)�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���ڡ�ϴ���g��֮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ġ���
�硷���� 2004 ���һ�졷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Ҳ�ǡ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^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Ĵ�����Ʒ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ʮ���»���ϵ�Єt��һ�N�O�˵�Ů�����Ҍ�(sh��)�(y��n)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Ů�����h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ڵġ����ᡱ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ȵġ����֡�ϵ�еȴ�đ�Lԇ������ҕ�X��Ůͬ�ԑ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Ҳ�ǡ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ȇLԇ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ħ�ú�����֮�g�ij��(y��n)ҕ�X���[����һ�N�Ї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ħ��ҕ�ǡ��n�I����
���DŽt�ڔzӰ�� Video 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 70 ��һ��Ů�Ե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X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 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γɵ�ˇ�g(sh��)˼��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Һͪ�(d��)���Ե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׳��J(r��n)�@һ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Κw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ͬ�ļ��w���L����߀�Ǵ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Ј���׃�Ї�֮����ɞ��c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z���vʷ��
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γ��µ�����ģ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 70
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ĺ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ڣ��@һ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ص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����ұ��_(d��)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ij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ǘӿ��]�c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
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 70 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ý�w�� Flash �Ӯ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X�ȷ��潨�����Լ�ҕ�X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^���ҕ�X��ʽ�����ڳ�Խ
1990
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(f��)�d�Ŀ��ܕr(sh��)��Ҳ���ɱ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_�źͿ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ͬ�r(sh��)ʧȥ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ǘ����܌��ښvʷ���ζ��ϵ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2005 �� 5 �� 23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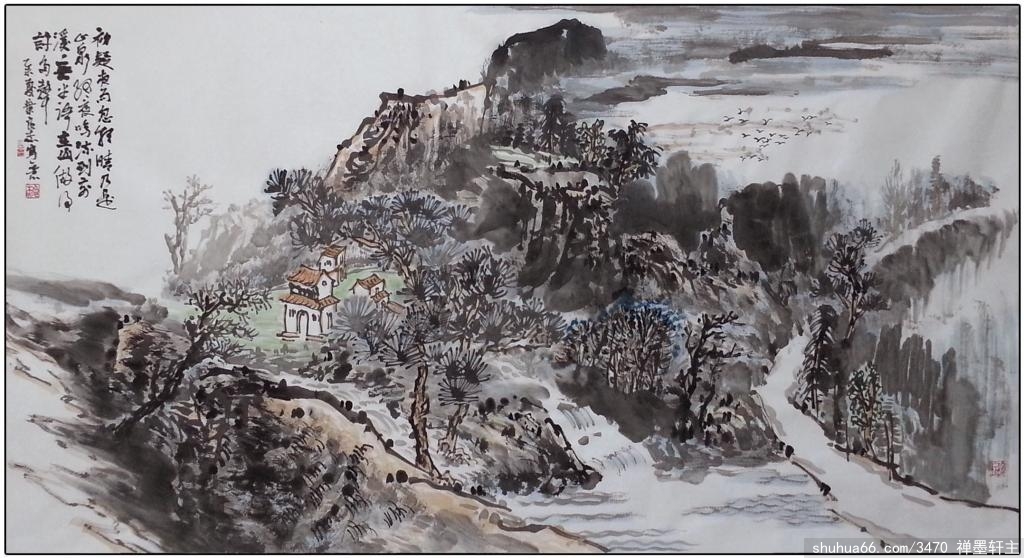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4 ���uՓ)